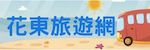電視政經節目名主持人王尚智談性騷擾案並論及傅崐萁被指性騷疑案幕後疑點
記者田德財/報導
電視政經節目名主持人、資深作家王尚智, 20日在臉書發表六千多字的評論文章, 論述性騷擾案,並談及傅崐萁被指控疑案。

照片均取自王尚智臉書
貼文說,性騷擾案除了有國家「司法犯罪」的判定層面,也有社會「道德價值」的集體層面,更也有諸如影視領域的「權力架構」的運作層面;權力關係不只是上下與男女,有時還有許多內幕細節。
以董成瑜舉發傅崐萁的例子,許多人就很難相信,堂堂身為「鏡傳媒/壹週刊」媒體集團的高層主管,手握狗仔及媒體生殺大權,為何能夠足足9年多來「沒有動靜、沒有反擊、沒有對付」,如今卻在傅徹底緊咬NCC護航鏡電視的背景下提出?
而傅崐萁為何會在一幫黨政大老、媒體頭頭面前,會去「抓頭親吻」與他根本不熟悉、政治立場敵對、同時在大學與媒體圈都以「高冷」著稱的媒體女高管?
也因此,舉發或舉證性騷擾的本身與當事者,也同樣會被社會與大眾「深度檢視」!
舉報者同樣不能以為「自己是絕對弱勢」,就能據此「一味取得大眾同情」或者「社會必須絕對支持」。

照片均取自王尚智臉書
以下是王尚智貼文全文內容:
性騷擾案發生至今,並不讓我驚訝,嚴格來說都是小咖。
但這裡有著社會事件延燒與滋長所需要的一切「能量」,脈絡且與國際上此前的發展相當一致。
說來都是一個人發生在過去幽微處的「一念貪欲」,當時一度蜷伸,但終於炙釀成罪業,如今反撲而來,打擊自己的名聲而破碎!
簡單說,真的就是所謂「#業力引爆」。
今天黃子佼的相關新聞繼續著,每一家媒體都做了同時超過了10篇報導。
也都是因為他自己在道歉的直播中,言行反而暴走大掃射,點名也點燃了更多騷動、觸及更多娛樂圈「往事的揭發」!
黃子佼原本雖然「因貪(慾)而傷」,但這個關鍵時刻,卻更是「#一念嗔燒毀功德林」!
所謂「言靈」,指的是言語有靈力,黃子佼是靠講講話吃飯的人,這次他遇到的生涯劫難,卻是一字一句將自己所有的關係斬斷,將自己推向深淵的人!
業力總是因「一念又一念」的錯誤抉擇,才會再三引爆。
危機無常當下驟臨,先要冷靜,莫讓自己在背後念念砍殺自己。
我認為除非小燕姐能給予巨大慈悲的能量灌注與修補,否則黃子佼已經注定此生,名聲徹底破碎。
國際上「MeToo」 運動,當初揭發比例最高的一直是「#演藝娛樂圈」!
這個以博取「眼球、人氣、名聲」,集體以「創造作品」而向著人心市場供需的領域,始終是以「幕前/明星價值」(Screen Value)與「幕後/資本運作」,兩者彼此相互主導與駕馭。
這當中也因此形成出,娛樂圈所獨特的「權力架構」,以及「階層往來流動」的模式,堪稱非常容易發生或者滋養性騷擾!
娛樂圈不只男女、男男、女女皆經常冒出騷擾,言行界線之中夾雜著欣賞、曖昧、愛慕各種紛混;一旦四下無人、一念所動,或借酒裝瘋!
影視文化是一種符號與意識的「人心滲透」,核心推動的力量本質是:「#名氣」。
影視娛樂圈,當中需要大量的不同角色分工設定,進行各種創意的流動與執行。
於是在所有作品完成之前,無數不為人知的日夜角落,進行比任何行業更多的人際往來「溝通」,一個眼神、一個伸手幾乎就可以觸及騷擾定義的邊緣。
也因此,各種難以想像、隨時冒出,甚至鋪天蓋地的「人性貪婪、情慾擴散、角色霸凌」,始終是影視圈子,要比其他專業領域更為無所不在的橫流肆虐!
韓國「Me Too」運動中,影視圈性騷擾充斥著的,都是導演、主角、製作人、投資老闆的惡業滿貫,幾乎是一種「隨手可得」的共同習性了。
每一個圈子,都有各自的「名、利、權」各自交相運作的邏輯,以及流動。
不得不說,發生許傑輝、宥勝、黃子佼之所以會被披露出性騷擾,並不是因為他們在這個圈子裡更有名、更有利、更有權。
相反且諷刺的是,反而有可能只是因為他們是「相對的弱勢、相對的善類」!?
簡單來說,許傑輝、宥勝、黃子佼均非影視圈呼風喚雨的一方之霸,他們無論形象上與能力上,反而是這個圈子裡比較可以「#被反擊的對象」!
受害者相對而言,可以用「最高的心理狀態、最低的現實成本」,挾著如今輿論媒體的關注熱潮未退,對他們進行最具槓桿效應的打擊。
於是接下來值得觀察的是,有多少「綜藝大哥(或大姐)」傳聞多時的性騷擾,才會被真正翻出?!
性騷擾本身的舉報,是否也有這麼一點「專挑軟柿子」的本能取向?
還有,今後開始有多少被舉報的「騷擾者、加害者」不會再沉默挨打,而將會毫不客氣的進行公開反擊?
事實上,這其實也是歐美「Me Too」運動經驗中,後來所微妙呈現的一種現實的諷刺與反轉。
其一,是真正被揭發的「幕後大鱷、幕前大腕」幾乎寥寥可數!這不是一個「平等普遍的運動」,而是「#有所選擇的揭發」。
其二,是性騷擾本身充滿太多「主客觀的界定模糊、事前事後的態度不一、精神傷痕的真假難辨」等等各種虛實差異!
一切的「傷害認定」都是因人而異,人生何處不相逢,人生何處無傷害?
除了那些確實長期造成身心精神障礙的受害者,那些當初明明「#已經勇敢堅強走出來」的人們,現在之所以又重新走回去,並且為何還能夠為此聲淚俱下,目的與意義何在?
性騷擾當事者們,一旦挺身在體制內申訴,乃至訴諸司法,這是讓人由衷敬佩的!
否則多數的揭發,似乎也並沒有完整期待或回向某一個「社會公義標準」,最終依然只是個案當事者「一時起意的傷痕回溯」。
而媒體與大眾關注目的「本質」,也依然還是符合或回歸於這個圈子的「原始機制」:「#一種特殊故事的獵奇」!
最明顯的就是,如今「新披露的性騷擾」不斷的覆蓋之前舊的,大眾沒有足夠的大腦容量記住所有。
第一起騷擾案的民進黨外包導演的「輝哥」,即使與蔡英文的交情與政商權錢未清,也已經沒有人有興趣了!
而舉凡後來是「小咖的性騷擾」,卻再也不會受到媒體與社群重視,因為性騷擾遭遇的「故事情節」,一旦讓人索然無味。
「Me Too」在國際上的演變,也都是因為以上這兩個「太多案子、小咖太多」核心因素,後來逐漸在人們的討論中來到無疾而終~。
我特別想分享,且整理我對這一波至今,台灣性騷擾的「綜合俯瞰」!一次思考完,之後就不多想了。

照片均取自王尚智臉書
***首先:
性騷擾事件本身確實容易出現大量的「#記憶錯植」,受害者不一定都是受害,這個失衡的現況,會慢慢改變。
當然,「Me Too」本身在國際上,後來也出現了好幾個「#結構性的被質疑」,值得思考。
比如經由宣稱的「受害者」,一個人自身的記憶回溯與事件敘述,往往也容易有偏失。
一方面,在許多時刻角落非常個人且隱密、難以成證。
另方面,所謂當事人的「回憶」,也有高度失真的可能。
包括對於自身「情緒、傷痕、影響」的描述,往往也會有「故事化與誇張化」,或者「自我視角的蓄意放大」的心理學效應。
這也最終導致國際上依然傾向「#由司法訴訟判定」,據此成為最後社會對性騷擾案的認定,而並非「全聽當事者的一面之辭」!
從現實層面而論,性騷擾也「#必須被證明」,這是核心關鍵!
1.)舉凡沒有任何「通訊/對話/道歉」的文字與記錄,或者2.)沒有任何「目擊證人、監視器畫面」;
尤其3.)受害者「沒有在事件發生當時與之後」,曾經有向外界第三方「哭訴、蒐證、看病、網路貼文紀錄」的具體動作,最終都很難取得司法判決上的認同。
***其次:
「受害者」所描述性騷擾的「加害者」,有時候確實並沒有所謂的逾舉行為,而是舉報者的「#個人恩怨報復」,甚至是來自某些「幻想、捏造」!
歐美「Me Too」運動最後尾聲,基本上是來到了強尼戴普與前妻安柏赫德的世紀官司,庭審拖延了數年。
最初安柏赫德指控強尼戴普的各種「騷擾、家暴、傷害」,幾乎使得強尼戴普被舉世唾棄,生涯瀕臨破碎,娛樂圈內與友人無不閃避。
但後來卻是經由眾多粉絲,從社群網路的各種「時空順序、圖文記錄」中,一步步找出安柏赫德的各種「謊言」!
經由長時間的言行比對,最終證明了所謂的「女性受害者」,壓根反而才是真正可怕「施暴者」,甚至是對於男性的「加害者」!
這起案子,也幾乎從此讓國際上對於性騷擾、家暴案「一面倒的相信受害者/女性」,從此嚴肅改觀。
.***第三:
性騷擾案件中有太多「#動機上變成為了蹭名氣」!
或者受害者一旦取得大量的社會「目光、同情、流量」,也開始情不自禁的踏入名氣的洪流,進行「流量變現」。
這點其實不限於性騷擾事件,台灣社會已經相當熟悉。
「洪仲丘案」就讓他的姊姊洪慈雍一路邁向政壇,隨機殺人的「小燈泡案」則是讓小孩的媽媽王婉諭也同樣踏入政壇。
從社會負面事件的當事人,後來卻因為爭議的「目光」,卻反而踏入影劇圈的更是不計其數。
整個流量變現的機制,來自媒體輿論的大幅報導,即使是「受害者」也同樣能創造出某一個特殊的「大眾符號」。
社會大眾一旦對於受害者「給予同情」,巨大到出現了質量轉變;尤其性騷擾案當中也幾乎都是「受害者才能獲得話語權」!
以朱學恆的性騷擾為例,讓鍾沛君獲得比她從政多年,還要更多、也更高的聲量與知名度。
在此之前,雞排妹甚至是新聞媒體圈是普遍被認定「非常熟悉,且懂得善用自己在市場形象的性符號」,乃至不斷創造各種「自己被性騷擾」,在爭議中不斷取得流量聲量的新聞事件當事者。
.說來我自己因為研究「Me Too」多年,性騷擾涉及的「社會價值、文化運動、媒體效應」非常微妙,一如性騷擾本身,非常幽微與充滿爭議!
***首先,
我個人更多是傾向從宗教上分析的「命運/業力」而去俯瞰這些遭遇與經歷!
這裡確實有許多「生涯/成敗」的無常與運勢之機妙!同時也皆有某些難以言說的徵兆與模式。
包括朱學恆、朱凱翔這幾位,都是我所相對熟悉的「新聞時事、評論領域」的朋友。
雖然沒有私下深交,但他們幾乎都是因為喝酒,最終「一念湧上」的慾念言行,而為此付出巨大的生涯摔落!
以「名聲」立足於世的人,幾乎都禁不起社會名聲一旦碎裂。
雖然也有能夠以「負面符號」安身立命的人,卻是少數中的少數
.***其次,
對於當今那麼多性騷擾案的舉發與披露,我自己始終保持「不信任、只聆聽、待觀察」!
因為從心理學臨床上,記憶回溯其中有太多的真假虛實,特別是一旦涉及了往往非常不可靠的細節因果。
對於所有性騷擾的受害者,倘若沒有真正「訴諸法律、申訴程序」,所有情節的描繪、傷害的敘述、情緒的發洩,基於此刻社會輿論的一味傾斜且少有平衡查證,我都有所留。
性騷擾案除了有國家「司法犯罪」的判定層面,也有社會「道德價值」的集體層面,更也有諸如影視領域的「權力架構」的運作層面;權力關係不只是上下與男女,有時還有許多內幕細節。
以董成瑜舉發傅崐萁的例子,許多人就很難相信,堂堂身為「鏡傳媒/壹週刊」媒體集團的高層主管,手握狗仔及媒體生殺大權,為何能夠足足9年多來「沒有動靜、沒有反擊、沒有對付」,如今卻在傅徹底緊咬NCC護航鏡電視的背景下提出?
而傅崐萁為何會在一幫黨政大老、媒體頭頭面前,會去「抓頭親吻」與他根本不熟悉、政治立場敵對、同時在大學與媒體圈都以「高冷」著稱的媒體女高管?
也因此,舉發或舉證性騷擾的本身與當事者,也同樣會被社會與大眾「深度檢視」!
舉報者同樣不能以為「自己是絕對弱勢」,就能據此「一味取得大眾同情」或者「社會必須絕對支持」。
***第三,
我認為性騷擾必須要被「#平等檢視」!
性騷擾既然大多發生為「潛規則」,那就需要社會人心可以相對依判的「明規則」,才能給予最大事實的靠近與平衡。
這當中包括了舉報者/受害者,她們最關鍵的「自我看待」。
「同情」與「無視」,雖是天差地別,卻有時同樣助長了扭曲!
遇到性騷擾,倘若沒有「當場拒絕、即刻反擊、事後申訴」,在現代社會而言究竟這是一個「弱者」,還是「無知者」?
加害者與受害者,內心其實都有潛在運行的一種「行為邏輯」。
不只是在性騷擾的當時,也包括了事後,乃至如今被舉報的此刻「如何(危機)處理」。
主要原因還是在於:我認為生命遭遇中一切遭遇的傷痕,雖說都是「個人絕對體驗」,但無論如何「#現實人生都必須繼續向前」!
最終當是「當事者的一念抉擇」!包括被指控的加害者亦然。
黃子佼惴惴不安許久,終於遇到了也爆發了,但卻依然沒有做好心理與現實上的「自我對策」。
直播暴走已經相當不智,然後又繼續自殘住院,一路不智下去
所以我也支持包括朱學恆在內的「#加害者」,以最終的司法調查判決,去為自己的過錯「訂定代價的標準」!
司法上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鍾沛君當時,有沒有已經正式接受朱學恆的道歉」?這將從根本上釐清道德之外,所有涉及的責任與代價的範疇界線。
也因此,這當中被指責是第三方「#包庇者」也是,也都應該努力為自己「尋求公道」!
而不是當今輿論、媒體與社群中只有充斥一味到底的「譴責與獵奇」,現實的體制運作與受害者的內心感受,也都同樣立體複雜。
我們處在這個需要廣泛運行著、也需要回到現實的「社會」與「人心」之中,我們旁觀者和每一位「受害者」都相同,都不能一直「深陷在性騷擾案」!旁觀者也需要釐清、判斷、思考的不同角度。
不能只是「沉溺於這些案子發生的過去」!乃至也不能只是「非要所有人與某一個人的傷痕一起無盡盤旋」!
性騷擾風波在台灣已經超過半個多月,從民進黨開始,如今娛樂圈的注目已經取代了政治效應。
台灣的「社會集體」對於一切,包括性騷擾,往往都只是一時的「意識騷動」而已。
而包括性騷擾事件中有太多「當事人」,每個階層領域也都存有各種「真假虛實」的內幕與層次,需要我們延長一不小心就「太快認定了對錯」,而沒有給予冷靜的洞悉與俯瞰。
所以我認為無論如何,「#司法判決仍然作為最後界定」,最終需要被優先尊重!
該追究的就追究到底,該翻頁的則依然就該速速翻頁。
這個世間與人間、這個台灣與社會,「比性騷擾更重要的事」始終多如牛毛!
要比性騷擾更嚴重、更值得同情關注的「基層角落苦難」,猶然還在大眾與媒體目光無視的邊緣,才具備了真正的不可抗拒。
身為男性,回顧一生,我自己也遭遇各種性騷擾大大小小數十次!
但我沒有覺得造成了什麼「傷害」,最終只是讓我清楚了人性「一念貪欲」是如何由小擴大、或者經常「因酒放大」。
教育界與宗教界也都有非常多的性騷擾!道德訴求或表象越深刻的地方,人性的貪婪往往潛藏越發的熾盛!
然而情慾在本質上,都是一種「貿然的虛無」。
我也從來不認為自己的身體「彷彿神聖不可侵」;明明健康與無常,乃至曾經的宵夜與熬夜,自己才是自己身體最大的傷害者。
如今整個社會彷彿都在鼓勵且一味同情著性騷擾的「受害者」,雖說這也確實讓許多「走不出來」的脆弱內心,獲得了支持與溫暖。
然而我認為,性騷擾的「此刻舉報」本身,與性騷擾當時一樣,都是一種巨大的傷害力量。
「公開舉報性騷擾」是透過挾著輿論大眾的目光之力,本質上亦是「手刃騷擾者」!據此讓「加害者與受害者,就此角色對換」!
性騷擾案一旦涉及了犯罪,我認為應該取得「公平正義」,那就「訴諸司法」吧!
我也無法理解或接受,如果在當初就已經政治「#接受道歉且表達原諒」的當事人,為何現在要訴諸大眾,再次將性騷擾事件翻出?
難道只是因為「一時感觸」?但這個感觸所造成對「對方無辜家人的傷害」,又完全可以理直氣壯、能夠不必在意?
如今社會上,並沒有太多人去質疑「揭露的行為本身與各自差異」?
至於性騷擾的「真正傷害」究竟如何?有沒有傷害,也因人而異。
嚴格來說性騷擾「發生在過去」,而一個人要「如何看待過去」?
是性騷擾傷害了自己,還是所有的傷害其實來自「#自己不原諒自己」,在當時或事後竟然無所作為?
每個人都有各自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之傷、之痛,所有這些人生所謂的「重、傷、痛」,有沒有可以「自己調整、賦予定義、重新抉擇」的詮釋空間?
於是,每個人是否應該「將某一個已經結束的過去,不斷拉回到現在」,並且「不斷佔用著自己與別人的現在」?
至少我自己不是這樣的人,我認為「#走出傷害」才是最關鍵!
才應該是性騷擾案社會思考討論的重點!也才是真正值得研究,且對人生與社會有真正幫助的事!
如果只是靠著不斷揭發過去,只能透過此刻,去「#傷害對方的現在如此才能走出自己的過去」,坦白說這樣也沒什麼意思。
特別是那一些不斷發新聞、不斷通知記者補充說明、二度三度道歉,擺明了就是藉此「蹭流量、博同情」,乃至那些一旦「移植情節、捏造故事」的性騷擾案,那就更沒意思了!